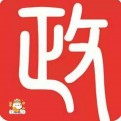陶校长的演讲里的题
问题描述
- 精选答案
-

“文玉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劂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司马迁自己也是宫刑余生著成《史记》。凡此种种,体现了学人之为人的根本,他们“读书不肯为人忙”的传统学术精神在生命的极端境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读书不肯为人忙”本是志洁心高的陈寅恰先生抗战前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毕’业生赠言”中昭告后人的“平生所学”的唯一“秘方”。有此精神,就不会曲学阿世,因为它要求人格、生命、学问的合一。有此精神,才会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真理。这种精神是无数代真正学人一脉相承最本质的东西。但是,自古以来,真正实践这种精神并将学问与生命融为一体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在古代做到学问与生命的统一,“读书不甘为人忙”是很难的。如果在思想领域非要找出什么特例的话,有两个人有必要一提。一个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稽康,他反对礼法,排斥六经,“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稽康传》,最终为司马昭公开处死于刑场。一个是明代的李贽,他“见道学先生尤恶”。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76岁高龄上在狱中以剃刀自刎。他留给后世的《答焦漪园》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他死后,他的《焚书》、《续焚书》等著作在明清两代均被列为禁书。这两个人是把学问与生命看做一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端。说到李贽,也就不应忘了和他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瑞士的卡斯特利奥,这个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中的人物不是一般中国人所知道的,但他奋起挑战的那个人在我们可谓声名赫赫一一欧洲史上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这个微不足道的卡斯特利奥竟敢于在“绝对正确”、享有巨大权力并且十分危险可怕的加尔文面前坚持己见。他身后也留下一句名言:“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偌使他和李贽有机会相识,他们”定会相见恨晚,以至于会引为知音的。可见,传统的学术精神为人类普遍具有。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布鲁诺纵然被焚也不改初衷;伽利略虽被边具结悔过,临走时仍大喊:“它仍在转动。”这些无不证明生命是学问的真正动力,学问与生命一旦相背反。就无法产生伟大深刻的思想。就会缺乏追求真理的热情,因而必然会逐渐支离破碎,走向衰败没落。其实,学术发展需要严道路实,实事求是,这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没有生命的真诚与投入,没有大胆的想象与创造,没有深刻独到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学术的发展。近代学风日益空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们急功近利,忘了起码的学术规范和道德,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再视学术为生命,而只是将学术当做求功名利禄的手段,“著书皆为稻粱谍”。魏晋学术的思辨与清谈之间的关系,唐代学术的开明与儒学复兴之间的关系,宋代学术的精深与宋儒崇尚气节之间的关系。以及清代学术考据成就斐然与经世思潮之间的关系,这里没有详具的必要。学问一但大而无当,连一个有代表性鲜活的生命都找不出。东拼西凑到这里,感到极为惶恐:这种浮而不实的探讨学问的态度度,恐怕是对学问与生命的不恭。还是就此停笔吧! 花自飘零水自流 壹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洕除 才下眉头 又上心头